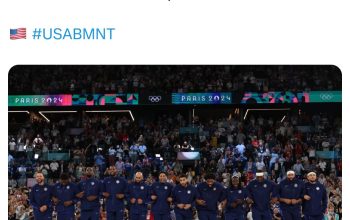2020年1月、3月、7月、12月,一年四季;在籃球人眼中,是一年四「封」。
鐵鏈封印籃球架成抗疫的手段,期待解鎖,但也害怕染疫。這是第四次,而我們都仍死心不息,畢竟籃球場曾經是一種必然的存在。
如今,球場「解封」,出現比平日街場更多的人流,一個令人無言的荒謬現實。
甲一、大專、學界,球員和教練每天不是忙着球會練習,就是練校隊。每晚,街場上一聲「跟隊」,不管是穿橙色青訓背心的男生,還是挺着啤酒肚的中年男人,都在同一地上揮灑汗水。學生也好,打工仔也罷,籃球就是生活。
只是不知從何時開始,香港沒有了籃球,只剩籃球人當年今日的限時動態,問得最多的一句是:「幾時?」。

籃球架上的鎖,困住籃球人的牢。(張倩儀攝)
跟葉耀邦、龍子傑再次踏入球場,他們說沒有感覺,因為太久,即使眼前球場成了花市,好像也很合理,「只係被習慣,變得逆來順受⋯⋯」
大家沒有放棄籃球,只自覺無能為力。同心抗疫本是義務,世界的確紛亂得容不下體育;世界體壇大事奧運可以延期、亞洲盃外圍賽可以因場地處處碰壁、準備出戰的港隊也沒有球場訓練,為抗疫而封場也變得更理所當然。

球場上有「水馬」、鐵欄、保安和警察,還有兩個被趕走的球員。(袁志浩攝)
「好想打比賽,幾時開返波?」
1月,政府宣布「對公共衞生有重要性的新型傳染病預備及應變計劃」,包括關閉體育館;學界分區決賽過後,所有賽事都因為疫情和場地問題,頻頻傳出延期或取消。「好快就會回復正常吧」只見學生球員一邊祈求比賽重開,一邊到街場消磨因練波取消多出的時間。
退而求其次,轉用街場,稍稍暫停球隊的訓練重新開始;就算戴起口罩打球呼吸困難,要多帶酒精消毒,大家照做不誤。沒有體育館,沒有比賽,街場,還是讓大家找到一點慰藉。

沒有防守者的場上,有桃花?(袁志浩攝)

籃球場不能打籃球,淪為花市入口的等候區,是不是叫「滑稽」?(袁志浩攝)
「封場?但應該很快就會開吧?」
3月27日,香港全面關閉免費戶外運動設施。前一晚,籃球人紛紛出門,「捉住打街場的尾巴」,因為翌日的籃球場,迎來從未有過的安靜。「好想打波!好想打波!」Instagram上幾乎每天都會出現的一句,大家爭相分享往日打球的照片;每天4點,總有一絲期待會提起球場重開,只是延後了一周又一周。
然而,一封就是三個月。
不敢相信Instagram上愁雲慘霧,來自一群熱血、正能量的籃球人,雖然輪番「放負」,字裏行間卻仍然抱有希望。6月重開,脫韁野馬重獲自由,籃球人回到球場,只是快樂的時間過得特別快。「夏天到,疫情可能就會明朗一點,當天SARS⋯⋯」當年經驗今次並不適用,7月上旬,疫情爆發第三波,球場?再次無一倖免。

「幾時?」到了這一刻,你還敢問出口嗎?(張倩儀攝)

到底在球場上,誰才是不速之客?(袁志浩攝)
「有得打好打了!」
面對每天新增的感染人數,籃球場再封,明白且無奈。不過區區封場,難不到平日下班練球的堅毅香港人。沒有街場,還能跑步、做體能,到公園拍波甚至四出找一些偏僻尚未封框的球場。一種既想分享打籃球的喜悅,又生怕大家知道「私家場」位置的矛盾心理,照片拍着籃框卻又要寫著一句:「不要問(在哪)」。
連做運動,都是偷偷的,不動聲色。
相隔一個多月,球場解封,籃球人又再次雀躍的往球場跑,只是大家心中有譜,知道事情只會沒完沒了——「有得打好打了」,放工好累、好遠、好多人⋯⋯通通不再是放棄的藉口,因為一想到明天又有可能封場,就更懂得珍惜當下。

看著市民經過籃球場,走入足球場買花。(袁志浩攝)
「哦,封囉。」
果然,二不離三,還來了第四次。入冬的日子,籃球場又再冰封,「心都涼了」更貼切不過。反應不外乎苦笑和「唉」,因為心中有數,所以對封場消息,做不出更大反應。
這一年,感同身受着政府所謂的新常態,第一和第四次封場,同樣的天氣和措施,大家態度截然不同。

如果是「正常」的球場上,他們可能不會看到大模廝樣橫過球場的人。(袁志浩攝)
限時動態上分享新聞,外加一句:「又封,慣咗」,分享的不再是打球的舊照,也不再問「幾時?」甚至知道當球場重開是為了花市,大家敢怒不敢言,麻木地只變成一句「係咁㗎啦。」就像龍子傑所說的:「成件事就是滑稽。」
「你說不想球場有人群聚集,但你看花市有多少人?堂食只可以開到6點,但花市卻能開到12點,根本就是自打嘴巴。」葉耀邦一言道破。

就像籠中鳥,哪裡才是出口?(袁志浩攝)
花市預計入場人次200萬,大概是街場全盛時期也累積不到的人數,然而事實是籃球場只容賣花,不容打波。「不知道由什麼時候開始,在香港打波好像做賊一樣。」龍子傑苦笑道。是的,這一年的香港籃球就像啞子吃黃蓮,窮得只剩下無力感。
每年新年,球場轉為年宵花市,球員都會放下籃球,走入一個不屬於運動的球場,參與應節活動;今年新年,同為市民的籃球人,在場上除了感受到荒謬、不解,大概沒有半點喜悅和節日氣氛。
為了抗疫,籃球場不能打籃球;因為節日,籃球場可以賣花。

封起的框又何時再見天日?(袁志浩攝)